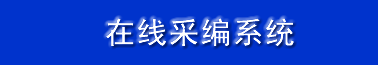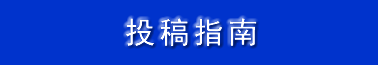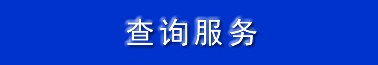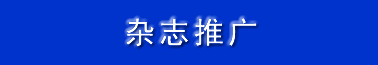项目支出预算激励机制分析:多任务委托代理视角
陈 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在预算层面,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存在着一种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代理人的部门及其官员需要执行工作性任务和绩效性任务。而原有注重经济性指标的政绩考核方式,以及财政领域以增加项目预算资金规模为主要手段的激励机制,客观上引导了部门及其官员努力完成工作性任务而忽视绩效性任务。本文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固定额度、“基数+增量”和“以收定支”项目三种项目预算模式下,现行激励机制无法引导代理人将努力程度更多投向绩效性任务中,此时激励机制是失效的。因此,提高预算绩效管理需要更多从加强约束和监督机制上着手,改变预算分配固化格局,深化对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改进部门及官员政绩考核机制。
关键词:预算绩效 多任务委托代理 项目预算 激励机制
一、引言
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出发,财政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间存在着一种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具体而言,财政部门作为委托人,需要代理人部门完成两类任务:一是工作性任务。财政政策的实现需要部门通过财政资金的使用来完成,部门使用资金越多,公共物品供给量的增加可能就越多,财政政策效用发挥就越大;二是绩效性任务。由于财政资金的稀缺性,财政部门希望代理人部门加强预算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在财政预算管理现实中,重投入支出的工作性任务、轻绩效管理的绩效性任务问题存在已久。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存在于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上。原有政绩考核主要集中于经济性指标,如果部门能够获得更多财政资金,其对业务领域的投入程度就更高,相应会带来政府公共物品供给量的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GDP增长,部门及官员的政绩水平也将提高。因此,部门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财政资金的争取和使用上,对绩效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而项目支出预算作为部门开展业务、特别是实施重大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其金额往往较大。从经验上来看,上述问题往往较为明显的体现在项目支出预算上[2]。
因此,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项目支出预算激励机制,提高代理人对绩效性任务的努力程度,对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政绩考核体系将财政部门提交人大批准的项目支出预算金额作为对部门及其官员的激励措施,即努力程度越大,争取的财政资金越多,对部门及官员带来的政绩就更大。而在预算编制领域中,主要编制方法分为因素法、项目法以及项目法与因素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本文分析中,我们没有将因素法分配项目和新增项目未纳入分析范围,将其余的既有延续性项目按激励机制的不同总结划分为固定额度项目预算、“基数+增量”项目预算以及“以收定支”项目预算三种模式。
本文从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不同模式出发,借鉴郭科、顾昕构建的关于固定薪酬制、分成制和租金制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框架[4],分析不同模式下对部门及官员行为的激励机制问题,提出通过现有激励机制难以解决预算绩效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约束和惩罚机制,改进政绩考核方式。本文论述按照如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对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及在部门预算领域对该理论的应用进行文献综述;第三至第五部分分析了不同模式项目预算的激励机制问题;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委托代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初属于现代企业理论范畴。它源自于当时部分经济学家对于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体系中企业“黑箱”理论的不满。这一体系忽略了企业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而这些经济学家们则开始进入这个“黑箱”中研究企业组织关系和结构问题[5],而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工作就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一个最优激励机制来激励代理人[6]。委托代理理论由Wilson[7]、Ross[8]、Mirrlees[9]等几位主要的提出者开创,后续随着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深入逐步完善和成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从最初的单代理人、委托人和单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拓展至多代理人、多委托人、多层次、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等方向。
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米尔格罗姆(Milgrom)是最早研究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西方学者。他们认为,如果代理人执行多项任务的话,简单的单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于分析现实情况来说已然不再适用。与之前学者们研究的模式不同,他们的研究假设委托人要求代理人执行多个任务,而每个任务最多只存在一个信号指标,代理人的报酬是由每项任务的线性激励契约规定的,总报酬等于各任务的报酬之和。经过分析,他们认为,不同的激励机制或激励契约能够引导代理人在不同任务间分配努力程度;如果不同任务的可度量程度不同,那么对其中一项任务的激励程度应随着另一项任务可度量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如果一项任务是完全无法进行度量的,那么最优的激励机制是所有任务都不给予激励,即所有任务都赋予固定工资[10]。在两位学者开创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之后,很多学者沿这一思路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不同任务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时,如何设计激励机制以实现最优;二是当存在多个业绩指标时,如何设计激励机制以实现最优[11]。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Waterman和Meier等把委托代理模型扩展并发展至政治组织领域[12]。其中,许多学者对政府预算方向予以了深入分析。
在预算委托代理形式的研究上,夏鑫、徐静认为政府部门在不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即有多重委托人,又有多重代理任务[13]。Smith和Bertozzi阐述了预算管理部门与支出部门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利用纽约州的数据检验了相关推论[14]。程瑜在研究中认为,政府预算是公民与国家间基于委托代理的一种契约,而这种委托代理契约关系表现为部门内部和部门外部共六层委托代理关系[15]。杨宗原在研究中认为,部门预算中的委托代理契约体现在从公众-立法机构-政府-政府财政部门-政府职能部门的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上[16]。曹艳杰在研究中认为,部门预算中委托代理关系还体现在部门和下属行政事业单位间[17]。
在预算委托代理问题的原因分析上,陈其辉认为,政府预算是一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体现,而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源自于监督弱化和激励不足[18]。江龙分析认为,政府预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所有者虚位”问题[19]。
在预算委托代理问题的对策建议上,张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事业单位不同风险分担机制下预算规则设计问题[20]。王金秀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应用于政府领域,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因政府性质的特殊存在着一系列“悖论”。因此他在构建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强调,政府治理在给予代理人适当激励机制时,要坚持约束机制主导[21]。FredKofman和Jacques Lawarée研究认为,当惩罚和约束程度足够高时,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在利益上谋求一致性将是最优选择[22]。程瑜认为,在政府预算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目标函数上并不总是处于一致状态,因此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很有必要的[23]。朱柏铭、李春燕在研究中认为,由于政府预算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长期契约,因此激励措施容易造成“棘轮效应”,因此激励措施只能短期内取得效果[2]。曹艳杰通过模型分析认为,控制部门预算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需要通过强化监督强度、提高公开水平等方式实现[24]。
通过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政府预算、特别是部门预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大多分析了其中的多层次性,对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着墨较少;在分析部门预算委托代理关系中,通过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模式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通过项目预算验证激励不足和强化监督的研究也不多。因此,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项目支出预算激励机制分析,对政府加强监督约束和惩罚机制、改进政绩考核方式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提供借鉴。
三、固定额度项目预算激励机制分析
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存在着某一项目近年中每年的预算金额基本都不发生变化或变化较小的情况。这种项目的出现和保留,某种程度上是源于综合考虑整体预算资金规模、项目的重要程度、项目所在领域及部门、政治环境等一系列政治博弈的结果。固定额度项目一般来说额度相对较小,占项目预算总体规模比例较低。在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上,固定额度项目类似于给予代理人“固定薪酬制”。
假设财政部门为委托人,部门及其官员为代理人。代理人需要完成两项任务,分别为工作性任务1和绩效性任务2。在这里,工作性任务体现在利用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情况;绩效性任务体现于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完成情况。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程度分别为
由于项目为固定额度模式,即财政部门每年给业务部门编列的项目预算额度是固定的,因此在部门及官员的激励模式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固定薪酬制”。在这里,我们假设代理人得到的激励
而部门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
如果财政部门要求部门及其官员在两个任务上的努力程度要至少达到一定的值E,即
如果
如果
当
由此可见,在固定额度项目支出预算的情况下,部门及其官员在不同任务间分配努力程度与项目预算安排额度t无关,仅与执行两项任务不同的边际成本相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对于财政部门来说,它希望t值越小越好。因此根据(3)式,t值将会选择最小值
(二)对于部门及其官员来说,因为其获得的是固定额度激励t,所以在达到最低努力程度E之后,其有可能就不再付出努力。加之委托人有减少固定金额项目额度甚至取消的倾向,因此相当于其激励水平有可能逐步降低,其努力程度就更有可能下降。
(三)从任务的可度量性上分析,绩效性任务的主观性更强,可度量性相对较差,而工作性任务因其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情况上,因此可度量性更高。所以代理人更倾向于将努力程度投向于工作性任务。而此时根据(一)(二),固定额度项目预算模式下的激励机制无法引导代理人对绩效性任务付出更多努力。所以,这一机制是在预算绩效激励方面是失效的。
四、“基数+增量”项目预算激励机制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逐年增多,其所需的财政资金规模也会日益增大。而对于部门及其官员来说,为确保工作任务的完成以及实现政绩的逐年增长,加之为了保证其既得利益,他们对于项目预算的金额也希望在上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因此这就涉及到项目预算规模的一种增长方式:“基数+增量”。这种模式类似于预算编制过程中“增量预算”模式,但如果这里的“基数”变为零的话,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预算编制的“零基预算”模式。从另一个角度看,“增量”的预算安排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项目的重要程度、委托人以前年度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政绩情况,因此这里也涉及一定的政治博弈。如果在博弈中代理人取得了一定优势,其“增量”资金规模就会相对较大。所以,在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上,“基数+增量”类似基于代理人“分成制薪酬”。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米尔格罗姆(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融入了Stiglitz关于分成制模型[27]的部分要素来分析“基数+增量”项目预算激励机制。
在这里,我们假设委托人财政部门对代理人的激励模式为分成制,而其固定激励部分,即“基数”为t,而将产出的一定比例作为分成激励,其分成系数在两项任务上分别为
将绩效性任务的产出代入模型,主要是绩效性工作开展对于争取财政资金工作有一定帮助。同时,我们假设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的成本函数分别为
所以,此时代理人的收益为:
因此,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
代理人要求
所以,
因此参与约束可以表示为:
对(8)式中的
而对于管理者财政部门来说,它的效用函数为:
因此将一阶条件和约束条件代入(8)式,得出财政部门的最优激励机制:
将(10)(11)式代入一阶条件,得出:
从(12)(13)两式可以看出,代理人对两项任务付出的努力程度取决于
与此同时,根据参与约束条件
此时,如果
(一)上述分析中得出了
(二)上述分析中我们认为,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条件下,即使“基数”
所以,“基数+增量”项目预算激励机制也无法引导代理人对绩效性任务付出更多努力,这一激励机制在预算绩效方面也是失效的。
五、“以收定支”项目预算激励机制分析
以收定支项目是按照有关规定,根据部门某项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或罚没收入等的额度来决定某项项目支出预算的一种部门预算经费保障模式。这种经费保障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情况下对于组织财政收入、保障部门工作正常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预算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因此,《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7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等文件明确规定了逐步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中以收定支的规定,统筹安排原有相关领域的财政支出。从2016年起,我国已先后取消城市维护建设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草原植被恢复费、海域使用金、排污费、水资源费等专项收入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规定,同时要求新出台的税收收入或非税收入政策,一般不得规定以收定支、专款专用。而在政府性基金领域,《预算法》明确规定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虽然已经取消了一般公共预算项目以收定支规定,而且项目支出预算安排表面上已明确与收入情况脱钩,但实质上部分地区的一些项目支出预算安排额度依然参考了收入情况或与收入情况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把以收定支项目的激励机制类比为一种“租金制薪酬”。一般公共预算中取消以收定支规定的项目,如果其按照前述模式编制预算,某项收入额度减去其项目支出预算额度的金额就相当于其付给财政部门的“租金”。如果该项目预算安排额度等于甚至超出收入,就可以理解为“租金”为零或负。政府性基金项目因为其以收定支的明确规定,其“租金”相当于零。在如下的分析中,我们参考郭科、顾昕在Holmstrom和Milgrom模型基础上进行逆向调整后的建模。
假设某项目每年收入扣除支出后的金额为
将绩效性任务纳入代理人的收入函数中,主要是因为如果该项资金的使用绩效较高的话,社会公众及资金监督者对收取该项收入的容忍性将会更高,这对于以后年度收入的保障作用会更加大。
我们继续假设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的成本函数分别为
所以,此时代理人的收益为:
因此,代理人的效用函数
这里要求
而
所以
因此参与约束可以表示为:
对(19)式中的
对于委托人财政部门来说,其效用函数变为
此时财政部门希望的
将一阶条件代入(21)式得:
(一)根据(22)式可以看出,委托人财政部门所获得的“租金”
(二)根据一阶条件可知,代理人部门及官员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程度分别为
六、结论
本文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项目支出不同预算模式下的激励机制问题。在分析中,我们首先假设部门及其官员作为代理人要同时完成两种任务,即工作性任务和绩效性任务。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代理人更趋向于完成工作性任务。因此本文重点分析项目预算分别在固定额度、“基数+增量”和“以收定支”三种不同模式下,财政部门的激励机制如何引导代理人在两项不同任务间分配努力程度。
对于部门及官员来说,在固定额度项目预算激励机制下,其在两种任务间分配的努力程度情况仅仅取决于执行两项任务的边际成本的大小,而与这种固定的激励水平高低无关。在“基数+增量”项目预算激励机制下,因为工作性任务相较于绩效性任务的可度量性更高,这种激励机制会引导代理人向工作性任务上投入更多努力。在“以收定支”项目预算激励机制下,因为绩效性任务完成情况带来的增收效果不会高于其产出,因此代理人对于工作性任务的努力程度也将大于对绩效性任务的努力程度。所以,这三种项目支出预算模式无法引导代理人对绩效性任务付出更多努力,其激励机制也是失效的。
针对上述激励机制失效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从以下方面加以着手解决:
1.进一步加强约束机制建设。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在政府预算领域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情况下,激励机制是无效的或只在短期内有效。因此,在激励与约束并举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激励不足”问题,政府应该选择加强约束和监督来进一步提高部门及官员对于预算绩效工作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这种约束和监督可以体现在有关绩效管理制度上的对部门及官员的强制约束,也可以通过来自政府体系的内部监督和来自社会公众、人大等外部监督加以施行。但实践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外部监督的约束力往往更强。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件规定了“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重点强调强化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和监督问责,本文其实也从另一角度对该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
2.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在本文所论述既有项目的三种预算模式中,固定额度项目和“基数+增量”项目在实际中往往属于人为因素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环节作用较大的项目。而这样的项目在实践中往往使用效率相对较低,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影响和监督机制的约束力不足,分配方式逐渐固化。因此,应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小、散、乱”等绩效水平低下的项目,提高按因素法分配的项目占比,在资金管理办法中对资金分配方式、职责分工等提出严格要求。同时,加快《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修订工作,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工作的制度化水平。
3.改进预算激励机制和政绩考核方式。本文为分析简便,假设工作性任务与绩效性任务是完全独立的。从实际上看,两种任务间是有一定促进与制约作用的。因此,通过建立资金使用绩效与预算资金安排的挂钩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代理人加强对绩效性任务的努力程度。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可对绩效完成情况好的项目和政策在下一年资金安排上优先保障,对于绩效完成情况一般或较差的政策和项目在资金安排上进行重点把控或取消安排。同时,不断改善部门及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将政策和项目的绩效完成情况纳入部门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这也进一步呼应了本文最开始分析的原有政绩考核方式存在的不完备问题。
综上,文中三种模式的项目预算难以形成促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激励机制,需要我们在社会公众、人大、政府、财政、业务部门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解决原有方式的“激励不足”问题,推动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的真正建立。
参考文献:
〔1〕朱柏铭,李春燕.部门预算改革的一个新思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J].浙江学刊,2004 (6):157-160.
〔2〕郭科,顾昕.公立医院管理中的激励机制: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5(10):49-58.
〔3〕何亚东,胡涛.委托代理理论述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3):62-65.
〔4〕David E. M. Sappington. Incentives i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2): 45-66.
〔5〕Robert Wilson.The Structure of Incentives for Decentralization Under Uncertainty [M].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9: 171.
〔6〕Stephen A. Ros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134-139.
〔7〕J. A. Mirrlees. 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M] // Essays in Economics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4: 243-258.
〔8〕Bengt Holmstrom and Paul Milgrom.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991, (7): 24-52.
〔9〕刘鸿雁,孔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文献综述[J].财会通讯,2017(16):43-46.
〔10〕Richard W. Waterman and Kenneth J. Meier. Principal-Agent Models: An Expansion?[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1998,8(2):173-202.
〔11〕夏鑫,徐静.地方政府预算信息披露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J].山东纺织经济,2012,(7): 36-38.
〔12〕Robert W. Smith, Mark Bertozzi.1998.Principals and agents: An explanatory model for public budgeting[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Financial Management, 1998, 10(3): 325 - 353.
〔13〕程瑜.政府预算中的契约关系及其制度设计——一种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视角[J].财政研究,2008(11):28-31.
〔14〕杨宗原.部门预算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85-88.
〔15〕曹艳杰.我国部门预算委托代理问题的制度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21(3):74-76.
〔16〕陈其辉.政府预算的委托—代理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 (6):69-71.
〔17〕江龙.公共财政下财政监督产生的理论溯源[J].财政研究,2001(11):12-16.
〔18〕张青.公共部门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资产所有权、管理权和预算规则的确定[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3):116-141.
〔19〕王金秀.“政府式”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J].管理世界,2002(1):139-140.
〔20〕Fred Kofman, Jacques Lawarée. On the Optimality of Allowing Collus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1(3): 383-407.
〔21〕程瑜.政府预算监督的博弈模型与制度设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视角[J].财贸经济,2009(8):48-52.
〔22〕曹艳杰.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部门预算道德风险研究[J].财政研究,2010 (11):48-51.
〔23〕张勇.一类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J].现代管理科学,2005(9):37-38+12.
〔24〕田盈,蒲勇健.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机制优化设计[J].管理工程学报,2006(1):24-26.
〔25〕Stiglitz, Joseph E.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4, 41(2): 21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