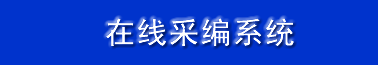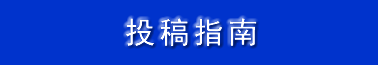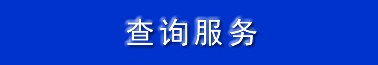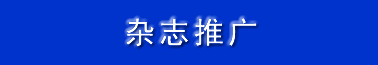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度
魏升民/广东省税收科学研究所; 成昊,黄亮雄/华南理工大学;向景/广东省税收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审视税收的高质量增长,能为考察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视角。本文构建了包含总量、速度、结构和效益四维度以及若干项基础指标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并对十八大以来我国30个省(市、区)2013年-2017年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情况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税收质量的稳步提高,更多地是来源于效益维度的显著改善。在趋同性和发散性检验中发现,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呈现显著的发散状态,表明区域差异在扩大,这主要源于效益维度指数的发散与分化,而结构维度指数呈现显著的趋同现象,表明区域差异在缩小;总量维度指数和速度维度指数的区域差异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从财税视角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并为进一步提高税收质量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 转移支付 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19)03-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2018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协调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科学评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不仅仅是要继续做好经济总量和速度核算、不断提高数据科学性准确性,更加要关注GDP的结构核算,及时准确地反映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许宪春、吕峰,2018)。
从相关研究看,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伴随经济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内涵外延(孙久文,2018;刘世锦,2018;任保平,2018;钞小静、薛志欣,2018;徐现祥等,2018)、结构优化(景维民、王瑶,2018)、动能转换(李平、付一夫等,2017;张月友、董启昌等,2018;陈昌兵,2018)等领域的研究逐渐丰富,一些学者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从不同视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师博、任保平,2018;魏敏、李书昊,2018;张自然、张平等,2018),也有一些学者强调财政税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并对财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Besley&Persson,2009;Jovanović&Klun,2017;林春,2017;孙英杰、林春,2018)。综合来看,上述成果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尚处在研究探索阶段;二是已有指标体系侧重经济、社会等宏观领域,虽设置了个别财税指标,但对财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明显不够,更没突出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因此,加快构建起反映财税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无论是对于总结近年来财税高质量发展成效,还是丰富和深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理论价值。
二、税收高质量的基本内涵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财税改革作为各领域体制改革的一个交汇点,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国家治理的所有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高培勇,2015)。审视财税领域高质量发展,可以透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考察高质量发展整体成效提供一个全新视角。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结合近年来财税领域发展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初步构建了一套包含总量、速度、结构和效益四维度以及若干项基础指标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30个省(市、区)2013年-2017年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情况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一)维度解释
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作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价方法(郭金玉、张忠彬等,2008),能够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将复杂问题转化为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对复杂问题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彭国甫、李树丞等,2004)。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并结合专家打分进行权重赋值。
首先,在建立递阶层次的结构中,根据高质量发展内涵确定指标选取原则,确定以税收高质量增长为目标层,选取总量指标、速度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四项指标作为准则层,也就是四维度,每项指标进一步分解为包含若干子指标项的方案层。
其次,四维度指标包括:①总量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税收收入规模、赤字比重等指标,反映税收总量规模情况,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在税收领域的自然反映②速度指标,主要包括税收年均增速、税收弹性等指标,反映税收增长变化情况,是衡量税收年度增长变化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增长阶段,更强调发展质量,但保持适当的中高速增长依然重要③结构指标,主要包括先进制造业税收占比、装备制造业税收占比、现代服务业税收占比、生产性服务业税收占比等指标,反映税收结构新变化④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单位GDP含税量、非税收入占比、财政收入变异系数等指标,税收效益的显著提升,是税收高质量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三,四维度指标中,总量指标是税收高质量增长的基础与起点,速度指标与结构指标是税收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体现,效益指标是税收高质量增长的深层次体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税收领域的自然映射。总体上,税收高质量增长四维度指标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诠释和彰显着近年来税收高质量增长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见图1)。
结构指标 总量指标 效益指标 速度指标 税收 高质量
图1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的四维构成
(二)指标形成
1.赋分设定。本文所涉及的方案层,即基础指标有20个,不同基础指标的计量单位不一样,需要进行去单位化处理。同时,为保证指标的年度可比性以及后续增加年份和区域的简易性。我们选取2013年全国水平作为标准,然后将各省份的各项数据均与全国水平比较,以产生分数。
第一,计算2013年各项指标的全国值作为对比对象,记为
第二,计算各省份各项指标在各年度的得分。设定
由赋分方法可知,我们以2013年的全国水平为基准,设定为60分,各省份各项指标,根据其与全国水平的比值进行赋分。例如,正向指标中,i省在第l项指标在第t年的数据是全国水平2013年数据的N倍,那么,i省在第t年在第l项指标的得分为(60×N)。
2.权重设定。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是一种综合多名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的综合评价实践中(徐蔼婷,2006)。本文采用专家打分赋权方法,邀请了6所重点院校的10位专家匿名打分,根据指标重要性给予不同的权重,重要性越高,则权重赋值就越大。所得权重是10人均值的结果,具体见表1。其中,总量指标的权重为12%,速度指标的权重为12%,结构指标的权重为40%,效益指标的权重为36%。由此,结构指标的权重最大,效益指标次之,总量指标第三,速度指标最末。
3.指标生成。具体的高质量增长指数设定公式如下:
选取2013年全国水平为基准,其它省份与之相对比来确定分数,然后生成总指标,主要有以下优势:一是便于做后续年份增加以及更多地区的对比。当前较为流行的标准赋分法,无论是最小值法、最大值法还是最大最小值法,都要选定所有数据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然而,随着年份的增加以及地区的增加,最大最小值会改变,导致数据量增加了,不同年份构建的指标以及不同地区构建的指标不能对比。本文以全国2013年的水平为基准,该基准不会随着年度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随着地区的增多而变化。由此,添加年份及地区后,并不影响不同年份、不同地区指标的对比。二是便于跨年份和跨地区的对比。由于选取的基准较为明了,各地区各年份指标与基准对比,就可以清晰地知道其与基准相差多少,改变了多少。由于基准就是全国2013年的平均水平,那就显示了各地区各年份相比于2013年全国水平的情况。如果使用上全国的年度变化指标,以及各地区的年度变化指标,既可以获得某地区在某年份处于全国怎样的位置,以及地区间对比又是如何。三是计算较为方便,化繁为简。无论是最小值法、最大值法还是最大最小值法,还需要经过一轮标准化,即两步标准化处理,第一步赋分,第二步标准化。这里采用2013年全国水平为基准,赋分和标准化只需一步完成。不但具有可比性与实际意义,而且化繁为简,操作方便。
另外,不同于以往随着时间变化和地区变化的标准化,其分数固定在0~100。本文的指标是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全国2013年基准的情况,由此,随着各地区的不断发展,所呈现的税收高质量指数得分也会出现相应变化,这并不影响本指标的数据。指数的绝对大小并没有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相对意义,尤其是能清晰地呈现年度趋势和地区差异。
表1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
|
目标层 |
准则层 (权重) |
方案层 |
单位 |
权重 |
指标性质 | |
|
正向 |
逆向 | |||||
|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 |
总量指标(12%) |
总税收规模 |
亿元 |
3% |
√ |
|
|
总税收占全国比重 |
% |
3% |
√ |
| ||
|
财政赤字率 |
% |
3% |
|
√ | ||
|
赤字占全国比重 |
% |
3% |
|
√ | ||
|
速度指标 (12%) |
总税收年度增速 |
% |
4% |
√ |
| |
|
总财政收入年度增速 |
% |
4% |
|
√ | ||
|
税收弹性 |
- |
4% |
√ |
| ||
|
结构指标 (40%) |
第二三产业税收占比 |
% |
4% |
√ |
| |
|
制造业税收占比 |
% |
5% |
√ |
| ||
|
先进制造业税收占比 |
% |
7% |
√ |
| ||
|
装备制造业税收占比 |
% |
7% |
√ |
| ||
|
现代服务业税收占比 |
% |
7% |
√ |
| ||
|
生产性服务业税收占比 |
% |
7% |
√ |
| ||
|
房地产业税收占比 |
% |
3% |
|
√ | ||
|
效益指标 (36%) |
单位GDP税收 |
元/元 |
6% |
√ |
| |
|
单位能耗税收 |
元/吨 |
6% |
|
| ||
|
单位污染税收 |
万元/吨 |
6% |
|
| ||
|
非税收入占比 |
% |
6% |
|
√ | ||
|
财政收入变异系数 |
- |
6% |
|
√ | ||
|
财政支出变异系数 |
- |
6% |
|
√ | ||
(三)数据说明
总税收及其分产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地区宏观方面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17年数据来源于全国和各地《统计公报》。其中需要注意几个基础指标。
一是先进制造业税收占比。由于《中国税务年鉴》的分地区分产业数据,并没有直接给出先进制造业税收数据。而且,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定义与划分,各个地区存在差别。我们采用制造业税收减去传统制造业税收,来表示先进制造业税收。其中,传统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二是装备制造业税收占比。装备制造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装备的各类制造业的总称。这里把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表仪器制造业定义为装备制造业。
三是现代服务业税收占比。现代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以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及居民社区服务业等为代表。那么,这里定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为现代服务业。
四是生产性服务业税收占比。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这里定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生产性服务业。
五是单位能耗税收和单位污染税收。前者采用地方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单位是元/吨标准煤;后者采用地产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是元/吨。
六是财政收入与支出变异系数。全国计算省级区域的变异系数;各省(市,区)计算地级市的变异系数。其中,由于缺乏2017年分城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2017年两项的变异系数,采用2016年数据×(1+2015-2016年的增长率);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没有下辖地级市,北京和天津数据采用山东和河北的均值,上海采用江苏和浙江的均值,重庆采用四川的数值。
三、指标体系测度结果及评价
根据上述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结合十八大以来我国30个省(市、区)2013年-2017年相关数据,构造出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及其核心的总量指数、速度指数、结构指数和效益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项指数的时间趋势、空间分布以及趋同变化情况。
(一)时间趋势
图2展示了我国及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从变化趋势看,2013年-2017年,全国及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税收领域的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其中2013年全国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标准化为60,到2017年,该指数提高到70.91,年均增长率为4.3%。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从79.97上升到175.38,年均增长21.7%;中部地区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从53.47上升到68.05,年均增长6.2%;西部地区高质量增长指数从52.28上升到61.84,年均增长4.3%。从水平值看,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第三。从增速上看,东部地区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末,且东部、中部地区增速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全国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提高,东部地区贡献最大。
|
|
|
图2 税收高质量增长总指数的时间趋势 |
进一步观察分维度指标的指数变化,在全国层面,出现明显提升的指标是效益维度指数,从2013年的60上升到2017年的86.50,年均增长9.6%,其余维度指数基本保持稳定,年均变动不超过2%。也就是说,近年来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提升,更多地源于效益维度指数的提升。与全国变动趋势相一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效益维度指数年均增速最快,结构维度指数变动速度最慢。横向对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情况发现,东部地区速度维度指数、效益维度指数增速最快,中部地区结构维度指数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总量维度指数增长最快,这表明东部地区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虽然总体领先,但中西部地区正在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
|
|
|
A.总量指数 |
B.速度指数 |
|
|
|
|
C.结构指数 |
D.效益指数 |
|
图3 税收高质量增长分维度指数的时间趋势 | |
(二)空间分布
参考相关学者采用分位数的形式(黄亮雄、安苑等,2013、2016),考察我国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空间分布。表2呈现了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区域分布情况,按指数大小进行降序排名,将30个省(市、区)平均分为四组,第1-8名为第一梯队,第9-16名为第二梯队,第17-24名为第三梯队,第25-30名为第四梯队。[1]
整体看,无论是2013年还是2017年,第一梯队省份基本集中于东部地区,第四梯队全是西部地区省份。其中,2013年,第一梯队中除吉林为中部省份外,其余均为东部省份,东部省份仅有河北不属于第一二梯队;2017年,第一梯队中仅有黑龙江不是东部省份,东部省份仅有河北不属于第一二梯队。
从首位省份排名情况看,2013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第一名分别是北京、吉林、宁夏,全国位次排名分别是第一、八、十一位,其中,北京的指数是吉林的2.57倍、宁夏的2.86倍;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第一名调整为北京、黑龙江、陕西,全国位次排名分布是第一、八、九位,北京的指数是黑龙江的7.20倍、陕西的7.86倍。全国排名第一位省份与排名最末位省份的倍数,从2013年的4.19倍扩大到2017年的12.92倍,这表明税收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省份排名位次变动情况看,中西部地区省份税收高质量增长呈现出省际分化特点。相比2013年,2017年排名位次升幅最大的省份是陕西,从第二十六名上升到第九名,上升了17个位次;排名位次降幅最大的是宁夏,从第十一名下降到第二十五名,下降了14个位次。
表2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区域分布
|
年份 |
梯度 |
指数范围 |
省(市、区) |
|
2013 |
一 |
65.46~168.24 |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吉林 |
|
二 |
55.76~61.03 |
福建、山东、宁夏、江西、青海、云南、新疆、辽宁 | |
|
三 |
50.79~55.49 |
湖北、河北、安徽、河南、湖南、甘肃、广西、黑龙江 | |
|
四 |
40.11~50.70 |
山西、陕西、四川、贵州、重庆、内蒙古 | |
|
2017 |
一 |
85.45~593.49 |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海南、浙江、江苏、黑龙江 |
|
二 |
69.98~75.54 |
陕西、福建、山西、山东、湖北、安徽、辽宁、江西 | |
|
三 |
62.50~69.62 |
青海、吉林、河南、河北、广西、湖南、四川、重庆 | |
|
四 |
45.92~62.46 |
宁夏、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 |
(三)趋同变化
图4以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来反映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区域差异。纵向观察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及其四维度指数区域差异的年度变化发现,2013年-2017年,无论是变异系数还是基尼系数,上升较为明显的是税收高质量增长总指数和效益维度指数,这说明两项指数的区域差异在扩大,呈现发散态势。其中,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变异系数从2013年的0.38上升到2017年1.07,提高了0.69,其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15上升到2017年的0.36,提高了0.21;效益维度指数的变异系数从0.82上升到1.70,提高了0.89,其基尼系数从0.29上升到0.55,提高了0.26。结构维度指数的区域差异在缩小,其变异系数从0.12下降到0.10,下降了0.02,基尼系数从0.062下降到0.056,下降了0.006。总量维度指数和结构维度指数基本保持不变。
|
| |
|
A.变异系数 |
B.基尼系数 |
|
图4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变化 | |
图5采用散点图的形式验证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是否存在趋同现象。图5-A采用面板数据,横轴是上一期的总指数,纵轴是总指数的年度增长率;图5-B采用横截面数据,横轴是2013年的总指数,纵轴是总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如果两图拟合线的斜率为负,表明该指数呈趋同态势,若拟合线的斜率为正,则表明该指数呈现发散趋势。由图5可见,无论是面板数据,还是横截面数据,散点图的斜率均为正,再次证明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呈发散态势。这与图4的结论是吻合的。
|
|
|
|
A. 面板散点图 |
B. 横截面散点图 |
|
图5 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趋同散点图 | |
为进一步检验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及其四维度指数的趋同性或发散性,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参考相关学者研究分别构建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回归方程(王贤彬、黄亮雄等,2017),具体如下:
(1)式采用面板数据,i表示省(市,区),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g_Tit为i省第t年的高质量财税发展各项指数(包括:总指数、总量维度指数、速度维度指数、结构维度指数和效益维度指数)的年度增长率,解释变量L.Tit为上一期的各项指数。
(2)式采用横截面数据,mg_Ti为i省2013年-2017年各项指数的年均增长率;T2013为2013年的各项指数。两式中,如果系数β显著地小于0,表明指数是趋同的;如果系数β显著地大于0,表明指数呈现发散趋势;如果系数β不显著,则上述两种现象均不出现。
表3分别采用了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其中面板数据采用了固定效应回归。对比两类回归,发现较为一致的结果:
一是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和效益维度指数的β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大于0,也就是,这两项指数是发散的,即初始指数高的地区,其增长速度更快,初始指数低的地区,其增长速度较慢,区域差异在扩大,这与图4和图5的结论一致。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发散与分化,主要是源于效益维度指数的发散与分化。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正加速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黄群慧,2014),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同步带动税收发展质量显著提升,然而,这种提升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即发达省份提升的速度更快,欠发达省份提升速度较慢,且不同地区内部提升速度也出现分化现象,这正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真实表现。
二是结构维度指数的β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小于0,表明结构维度指数呈现趋同状况。即初始指数高的地区,其增长速度较慢,初始指数低的地区,其增长速度较快,区域差异在缩小。这也与图4的结论是一致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种努力反映到税收领域,也更多地直接体现在结构维度指数层面,但结构调整的效益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才能逐步呈现出来,效益维度指数还在持续发散。
三是速度维度指数的β系数在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中,符号均为负,后者还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同时,总量维度指数在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中,符号均为负,前者还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虽然趋同现状并不明显,但只要坚持朝着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进发,可以预见,总量维度指数和速度维度指数的趋同态势将日渐明显,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也将逐步得到有效缓解,全国税收高质量增长也将得到趋同。
表3 实证分析检验结果
|
|
面板数据 | ||||
|
总指数 |
总量指数 |
速度指数 |
结构指数 |
效益指数 | |
|
β系数 |
0.004** |
-0.008*** |
-0.210 |
-0.009*** |
0.003*** |
|
|
(0.002) |
(0.002) |
(0.125) |
(0.000) |
(0.001) |
|
常数项 |
-0.159 |
0.380*** |
20.759*** |
0.562*** |
-0.062 |
|
|
(0.113) |
(0.101) |
(6.553) |
(0.030) |
(0.077) |
|
趋同/发散 |
发散 |
趋同 |
NA |
趋同 |
发散 |
|
R2 |
0.077 |
0.135 |
0.028 |
0.469 |
0.251 |
|
N |
120 |
120 |
120 |
120 |
120 |
|
|
横截面数据 | ||||
|
总指数 |
总量指数 |
速度指数 |
结构指数 |
效益指数 | |
|
β系数 |
0.003*** |
-0.000 |
-0.005*** |
-0.001** |
0.001*** |
|
|
(0.001) |
(0.000) |
(0.002) |
(0.000) |
(0.000) |
|
常数项 |
-0.110*** |
0.058*** |
0.395*** |
0.073*** |
0.052* |
|
|
(0.031) |
(0.013) |
(0.127) |
(0.021) |
(0.029) |
|
趋同/发散 |
发散 |
NA |
趋同 |
趋同 |
发散 |
|
R2 |
0.684 |
0.047 |
0.400 |
0.206 |
0.385 |
|
N |
30 |
30 |
30 |
30 |
30 |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小括号里为稳健的标准误;(3)R2表示拟合优度;(4)N表示样本量。
四、结论及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税收领域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更多地是来源于效益维度的显著改善。无论是水平值还是增速值,效益维度指数均明显高出其他分维度指数;在趋同性和发散性检验中还发现,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呈现显著的发散状态,表明区域差异在扩大,这主要源于效益维度指数的发散与分化,而结构维度指数呈现显著的趋同现象,表明区域差异在缩小;总量维度指数和速度维度指数的区域差异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
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起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税收体系。研究发现,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虽然在提升,但这种提升具有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创新发展的现代税收体系。一是降低宏观税负,处理好“积累与消费”“效率与公平”“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二是优化税制结构,处理好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结构性调整与结构性减税、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关系,稳步推进直接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深化税收职能,立足国家治理,促进税收向现代税收体系转型、从短期效率向长期公平转变,助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建立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本文研究发现,税收高质量增长指数总体上是发散的,区域差异在扩大。在财政支出特别是转移支付方面,要适当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一方面,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结合高质量发展谋划,统筹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另一方面,按照“有助于平衡区域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央宏观调控、有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目标,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尤其是要解决好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吕冰洋、毛捷等,2018)。同时,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等国做法,在总结省市援藏援疆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纵向转移支付不足。
第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是实施更大力度地精准减税降费改革,按照《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要求和中央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点领域税种改革。以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改革为契机,在税务部门全面摸清费源底数、完善费源管理、拓宽费基等基础上,为降低企业社保费负等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二是完善创新创业型税收优惠体系,加大对科技型、创新型市场主体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三是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税收营商环境。以贯彻落实放管服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全面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使我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位次达到0ECD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准。
参考文献:
〔1〕许宪春,吕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2018(8):4-19。
〔2〕李永友.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研究:江苏的经验——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8(8):113-118。
〔3〕Sabatini Fabio.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Kyklos,2008,61(3):466-499
〔4〕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6):75-86。
〔5〕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11(4):26-40。
〔6〕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7〕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8〕孙久文.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到高质量、平衡的区域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18(1):1-4。
〔9〕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8-2027):中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
〔10〕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及其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18(5):35-43。
〔11〕钞小静,薛志欣.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2-22。
〔12〕徐现祥,李书娟,王贤彬,毕青苗.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J],世界经济,2018(10):3-25。
〔13〕景维民,王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研究——稳增长、高质量发展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J],现代财经,2018(12):13-21。
〔14〕李平,付一夫,张艳芳.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12):5-21。
〔15〕张月友,董启昌,倪敏.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J],经济学动态,2018(2):23-35。
〔16〕陈昌兵.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5):16-24+41。
〔17〕师博,任保平.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J],经济问题,2018(4):1-6。
〔18〕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1):3-20。
〔19〕张自然,张平,袁富华,楠玉.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2018):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20〕Besley Timothy &TorstenPersson.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4):1218-1244.
〔21〕JovanovićTatjana& Maja Klun. Tax Policy Assessment Challenges: The Case of the Slovenian Interest Tax Shield[J], 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 Finance, 2017,28(5):27-40.
〔22〕林春.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财政研究,2017(2):73-83+97。
〔23〕孙英杰,林春.税制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地方政府税收合意性的一个检验[J],经济科学,2018(5):5-16。
〔24〕高培勇.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J],管理世界,2015(12):4-11。
〔25〕徐蔼婷.德尔菲法的应用及其难点[J],中国统计,2006(9):57-59。
〔26〕郭金玉,张忠彬,孙庆云.层次分析法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8(5):148-153。
〔27〕彭国甫,李树丞,盛明科: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权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6):136-139。
〔28〕黄亮雄,安苑,刘淑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中国工业经济,2013(10):70-82。
〔29〕黄亮雄,安苑,刘淑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企业兴衰演变的考察[J],产业经济研究,2016(1):49-59。
〔30〕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李郇.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动态趋势重估——基于太空灯光亮度的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7(3):877-896。
〔31〕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5-19。
〔32〕吕冰洋,毛捷,马光荣. 分税与转移支付结构:专项转移支付为什么越来越多?[J],管理世界,2018(4):25-3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