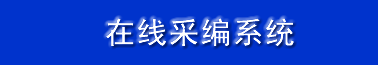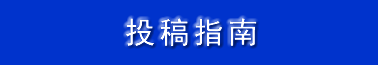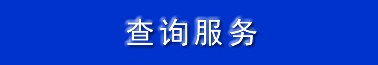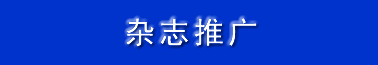朱柏铭/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与财政转移支付
浙江大学
内容提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就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受众将由户籍人口扩展到常住人口。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国大体形成了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和人口净流出—补助高溢入两大区域,新型城镇化将增大前者的财政压力。若转移支付的决定引入“常住人口”变量,人口流动与补助不匹配的格局有望改观。
关键词:人口净流入 补助低溢入 财政转移支付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Urbanization),本意是指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集聚。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不是空间(土地)的城镇化,也不是经济(产业)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就是以往所称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进城务工人员”。时期Ⅲ不是时期Ⅰ的简单回归。时期Ⅰ中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的主要鸿沟在于户口;而时期Ⅲ中的农村人口是指不愿意生活在城镇,在农村工作和生活更符合其偏好的群体。另外,时期Ⅱ中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渐成为城镇人口,以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前提,并不以拥有城镇户口为条件。
老一代农村人已经习惯于农村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只有新生代农村人才对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心向往之。所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要让新生代农村人融入到城市中,入学、就业、生活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经济活动市民化,缩小他们与户籍人口之间在就业、工资、消费等方面的差距;再如公共服务市民化,让他们在居住地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计划生育、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这就意味着,对于政府来说,过去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只局限于户籍人口,今后将逐步扩大到常住人口。
公共服务受益面的扩大,使东部的地方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今后拿什么钱给流入的农业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入到东部地区,而财政体制决定,东部又是向中央上解财政收入较多而获得转移支付较少的地区。诚然,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多种思路,如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或者中央与地方创新财政体制,重新划分事权和财力。
如果不改变经济水平和财政体制等约束条件,通过改革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决定机制,是否是一种出路。这是本文所关注的话题。
国内学术界有关于转移支付对财政能力差异的研究,如刘溶沧、焦国华(2002);也有关于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分析,如马拴友、于红霞(2003)。然而,专门探究人口流动与转移支付相关关系的文献,鲜有所见。陈仲常、董东冬(2011)合作的论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利用1995-2009年的数据,考察区域差异化的人口负担对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结论是,如果考虑人口总抚养比,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反而低于东部地区。另一篇相关的文献是由袁飞、陶然(2008)等人撰写的,他们利用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变量关系。
本文把全国区分为四种类型: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地区、人口净流入-补助高溢入地区、人口净流出-补助低溢入地区和人口净流出-补助高溢入地区。提出的假说是,城镇化将引致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地区财政支出的广化,若在转移支付决定机制中引入“常住人口”变量,有望减轻其财政压力,同时现有转移支付格局也更体现公平原则。
二、公共服务受众的扩展引致财政支出广化
长期来,各地政府都按照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公务员、官员、教师、医务人员等行政事业单位的编制,即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根据辖区内的户籍人口总量,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另一方面,医院、学校、剧院、体育馆等公用设施也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进行配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政府对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些发达国家就是按照辖区内的实际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例如警民配置比例,西方国家是万分之三十五,我国只有万分之十一,不仅比例上相差甚远,而且分母大不相同,前者是实际人口,后者是户籍人口。照理说,今后应该按照辖区内的实际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不过,从统计数据的真实度看,由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更为现实。[①]
主流公共经济学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新增一个消费者的边际分配成本等于零。事实上,大多数准公共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拥挤性,即便是国防事务,也与人口多少相关联,各国军事人员的数量与人口总量经常呈正相关关系。
布朗和杰克逊(Brown&Jackson,1990)曾用拥挤函数(Crowding Function)来表述人口变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
AK = XK / Nα (1)
上式中,AK表示第K种产品的效用;XK表示用于生产第K种产品的活动(费用或设备);N为人口规模;α是拥挤参数。在纯公共产品情况下,α=0,AK=XK,说明现有公共活动能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人口变化无关,无须增加财政支出。在私人产品情况下,α=1,即消费者增加会减少效用。在准公共产品情况下,0<α<1,人们获得效用有所下降,为保持效用水平不下降,财政支出要有所增加。
准公共产品与人口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消费者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会出现“拥挤”,即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增加会引起公共服务供给成本的增加。以下七类公共服务均与人口的数量或密度相关,地方政府若按户籍人口配置公共服务,在流入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拥挤;若按常住人口配置,则相应的财政支出会明显增加。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覆盖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要求增加各级各类官员及公务员,相应地,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会有所增加。
2.公共安全支出。武警、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监狱、劳教等直接增加社会的治安成本。邻里效应表明,人口流动性与治安有直接的关联性[②]。来自基层公安部门的经验数据是,四分之三的犯罪嫌疑人与农业转移人口有关。
3.教育支出。幼儿园、中小学,甚至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逐步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经费就会增加。
4.文化娱乐支出。设置图书馆分馆、充实藏书量、规划体育场馆,在中心公园、社区广场、居民小区设置健身运动器材等。
5.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提供免费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就业见习补贴、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补贴;救助家庭成员中非本地户籍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农业转移人口中的老年人可入住各类社会办养老机构;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和优惠乘车;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6.计生和医疗卫生支出。免费提供婚前检查、孕前检查、避孕药具领取等计生服务;增加公立医院药品、药具;增加社区医务人员。
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城乡社区管理、公共设施、住宅、环境卫生等服务。如农业转移人口中小摊贩很多,可能影响社区环境、道路通行、户外广告等市容环境,需增加城管执法支出。
可见,公共服务受益面的扩大,会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按照布朗和杰克逊的拥挤函数理论,在保持相同效用水平的条件下,实际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应与人口的增长率相等。笔者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财政支出广化(Fiscal Expenditure Widening)”。
三、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地区财政压力陡增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对比值衡量人口流动情况。结果发现,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河北、山西、海南、山东、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15个省(市、区)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余16个省(市、区)是人口净流出地区,包括:陕西、江西、云南、新疆、湖南、湖北、河南、重庆、广西、甘肃、四川、安徽、贵州、宁夏、青海、西藏。
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全国所有省(市、区)都获得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转移支付。但是,不同省(市、区)获得的补助数额相差很大(见表1)。
表1 2011年各省(市、区)人均转移支付
单位:元
|
省(市、区) |
人均转移支付 |
省(市、区) |
人均转移支付 |
|
西藏 |
23564 |
湖北 |
3342 |
|
青海 |
14302 |
江西 |
3312 |
|
宁夏 |
7397 |
四川 |
3310 |
|
新疆 |
6801 |
山西 |
3184 |
|
内蒙古 |
6323 |
湖南 |
3136 |
|
甘肃 |
5073 |
天津 |
3123 |
|
黑龙江 |
4862 |
安徽 |
3041 |
|
吉林 |
4763 |
河南 |
2673 |
|
海南 |
4736 |
上海 |
2617 |
|
(全国平均值) |
(4588) |
河北 |
2532 |
|
贵州 |
4408 |
北京 |
2507 |
|
陕西 |
4262 |
福建 |
2199 |
|
重庆 |
3899 |
山东 |
1783 |
|
云南 |
3743 |
浙江 |
1658 |
|
辽宁 |
3436 |
江苏 |
1545 |
|
广西 |
3434 |
广东 |
1252 |
注: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12》有关数据和常住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再从各省(市、区)财政自给率角度考察补助溢入情况。如前所述,所有省(市、区)都获得了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转移支付,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为“补助溢入”。按表2计算,全国各省(市、区)平均财政自给率为0.496。
表2 人口流动与补助溢入程度的对比
|
人口流动程度 |
类属 |
财政自给率 |
类属 | |||
|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
人口净流入 |
人口净流出 |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补助低溢入 |
补助高溢入 | |
|
北京 |
1.55 |
√ |
|
0.87 |
√ |
|
|
天津 |
1.30 |
√ |
|
0.83 |
√ |
|
|
河北 |
1.02 |
√ |
|
0.51 |
√ |
|
|
山西 |
1.02 |
√ |
|
0.48 |
|
√ |
|
内蒙古 |
1.01 |
√ |
|
0.45 |
|
√ |
|
辽宁 |
1.02 |
√ |
|
0.68 |
√ |
|
|
吉林 |
1.01 |
√ |
|
0.39 |
|
√ |
|
黑龙江 |
1.01 |
√ |
|
0.29 |
|
√ |
|
上海 |
1.68 |
√ |
|
0.88 |
√ |
|
|
江苏 |
1.05 |
√ |
|
0.84 |
√ |
|
|
浙江 |
1.14 |
√ |
|
0.82 |
√ |
|
|
安徽 |
0.87 |
|
√ |
0.44 |
|
√ |
|
福建 |
1.05 |
√ |
|
0.68 |
√ |
|
|
江西 |
0.98 |
|
√ |
0.42 |
|
√ |
|
山东 |
1.01 |
√ |
|
0.69 |
√ |
|
|
河南 |
0.93 |
|
√ |
0.41 |
|
√ |
|
湖北 |
0.93 |
|
√ |
0.47 |
|
√ |
|
湖南 |
0.94 |
|
√ |
0.42 |
|
√ |
|
广东 |
1.22 |
√ |
|
0.82 |
√ |
|
|
广西 |
0.90 |
|
√ |
0.37 |
|
√ |
|
海南 |
1.02 |
√ |
|
0.44 |
|
√ |
|
重庆 |
0.90 |
|
√ |
0.48 |
|
√ |
|
四川 |
0.89 |
|
√ |
0.44 |
|
√ |
|
贵州 |
0.87 |
|
√ |
0.34 |
|
√ |
|
云南 |
0.98 |
|
√ |
0.38 |
|
√ |
|
西藏 |
0.85 |
|
√ |
0.07 |
|
√ |
|
陕西 |
0.98 |
|
√ |
0.41 |
|
√ |
|
甘肃 |
0.87 |
|
√ |
0.25 |
|
√ |
|
青海 |
0.89 |
|
√ |
0.16 |
|
√ |
|
宁夏 |
0.86 |
|
√ |
0.31 |
|
√ |
|
新疆 |
0.96 |
|
√ |
0.32 |
|
√ |
资料来源:常住人口参考六普数据,户籍人口以2010年末为基准。现在好多省(市、区)都不公布户籍人口,所以户籍人口数据可能有误差,但对比值的排名影响不大。地方财政自给率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12》有关数据计算。
若综合考虑人均转移支付和财政自给率,以二者的全国平均值为界限,则属于补助低溢入的有:北京、上海、江苏、天津、广东、浙江、山东、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属于补助高溢入的有:山西、陕西、河北、重庆、湖北、内蒙古、安徽、四川、海南、湖南、江西、河南、吉林、云南、广西、贵州、新疆、宁夏、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等22个省(市、区)。
再将人口净流入、净流出因素相联系,可将全国31个省(市、区)分为以下几类: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人口净流入-补助高溢入、人口净流出-补助低溢入和人口净流出-补助高溢入(见表3)。
表3 人口流动与补助溢入的组合
|
类 别 |
数量(个) |
省(市、区) |
|
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 |
10 |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福建、辽宁、河北 |
|
人口净流入-补助高溢入 |
5 |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 |
|
人口净流出-补助低溢入 |
0 |
无 |
|
人口净流出-补助高溢入 |
16 |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的10个省(市、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它们上解中央的财政收入最多,还要承受对口帮扶的负担。以浙江省为例,2010年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2014年全省从中央获得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别为455亿元和524亿元,合计979亿元,占当年全国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额51605亿元的1.9%。全省实现公共预算总收入7522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21亿元。也就是说,上解中央3401亿元,扣除获得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979亿元,净上解中央2422亿元。一些流入人口较多的市、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例如温州市乐清市,是温州台州一带唯一一个规模工业产值突破千亿元的县级市。2013年公共预算总收入达到102亿元,但地方可用财力只有51亿元,仅占公共预算总收入的50%。该市户籍人口有128万人,流入人口最高峰时达到81.5万人。仅教育方面,乐清市政府每年支出17亿元左右,占地方可用财力的1/3。其中又有6亿元用于流入人口子女的教育,占教育支出的1/3。
再如宁波市,2011年户籍人口为574万人,市外流入人口达430万人,其中北仑、鄞州、镇海等区区外流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同年,宁波市地方财政收入657.55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50.72亿元,财政自给率为0.88,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有多少?“转移性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仅162.55亿元”[③]。笔者查阅了资料,2011年宁波市地方债券发行规模为14亿元。这就是说,宁波市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为148亿元,人均1474元,比表1中江苏省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还少71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宁波市的财政压力有多大?笔者恰好于2010年实地做过调查,在此罗列几项。(1)公共安全支出。如果宁波市警察数量和人口比例要达到1:500,则警力缺口还有7000人,按照每个警员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5万元/人/年计算,尚缺财政资金3.5亿元。(2)教育支出。按生均公用经费3000元/年,每年增加人数1万人计算,至少需新增教育经费3000万元/年。而甬外流入人口子女每年增加2.5万人以上。(3)卫生支出。儿童需接种“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三联制剂、麻疹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流脑疫苗”等七苗,即便不考虑人工费用和注射用具费用,仅疫苗成本就需要20元/人。防疫部门的资金缺口每年在280万元左右。曾有学者测算“十二五”期间宁波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规模,结果是人均需投入13507.4-25507.4元。[④]
巨大的财政压力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在转移支付决定机制中引入人口因素并加大其权重,或许是一个路径。J.Buchanan(1950)认为,转移支付应当以协调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为目的。Robin&David(1984)认为,转移支付应建立在横向均衡原则之上,使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都得到“平等的财政对待”。J.F.Graham也认为,之所以需要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是因为公共服务不可分割也不能完全根据受益原则提供。这些学者的观点说明,优化转移支付的配置可以缓解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地区的财政困难。
四、转移支付决定机制中引入“常住人口”变量
现行转移支付决定机制,虽然与人口有关,但是引入的变量是“户籍人口”。这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缓解财政压力很不利。笔者认为,应该引入“常住人口”变量。
1.现行转移支付与“人口”变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具体项目较多,不少项目与人口直接关联。从表4看,与人口关联程度紧密的项目有8项,涉及金额21399.98亿元,占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24538.35亿元的87.21%。
表4 2013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与人口的关联程度
|
序号 |
项目名称 |
预算数 (亿元) |
用途 |
人口关联程度 |
|
1 |
均衡性转移支付 |
9812.25 |
中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产粮大县的基层政府。 |
Y |
|
2 |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
621.90 |
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民生事业。 |
Y |
|
3 |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
2451.22 |
艰苦边远及高海拔地区的补贴。 |
Y |
|
4 |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
752.60 |
补贴农业税等改革的财力缺口。 |
N |
|
5 |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
194.00 |
资源枯竭城市的补助。 |
Y |
|
6 |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
714.00 |
补贴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缺口。 |
N |
|
7 |
体制结算补助 |
1274.46 |
企事业单位划转的补助。 |
N |
|
8 |
工商部门停征两费转移支付 |
80.00 |
收费改革的财力缺口。 |
N |
|
9 |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
494.60 |
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的补助。 |
Y |
|
10 |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
1821.19 |
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贴息等,县镇高中教育减债奖补。 |
Y |
|
11 |
基本养老金和低保转移支付 |
4342.51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
Y |
|
12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移支付 |
1662.31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Y |
|
13 |
村级公益事业奖补转移支付 |
317.31 |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奖励。 |
N |
|
|
一般性转移支付合计 |
24538.35 |
|
|
注:Y-与人口关联程度紧密,N-与人口关联程度不紧密。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3月26日财政部《关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说明》归类。
至于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目前多达18个,从表5看,与人口关联程度紧密的项目有10项,涉及金额15380.05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总额19265.86亿元的79.83%。
表5 2013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与人口的关联程度
|
序号 |
项目名称 |
预算数 (亿元) |
判别依据 |
与人口关联度 |
|
1 |
一般公共服务 |
259.50 |
保障地方“四套班子”正常运行。 |
Y |
|
2 |
国防 |
24.39 |
国防部门的补助。 |
N |
|
3 |
公共安全 |
244.88 |
公共安全部门基本建设的补助。 |
Y |
|
4 |
教育 |
1189.61 |
职业教育、地方高校补助、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
Y |
|
5 |
科学技术 |
68.15 |
重大科技专项资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补助。 |
N |
|
6 |
文化体育与传媒 |
303.65 |
国家文物保护,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文化人才补助。 |
Y |
|
7 |
社会保障和就业 |
1581.69 |
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优抚对象补助。 |
Y |
|
8 |
医疗卫生 |
858.92 |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
Y |
|
9 |
节能环保。 |
2007.57 |
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 |
N |
|
10 |
城乡社区事务 |
188.00 |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
Y |
|
11 |
农林水事务 |
5406.7 |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现代农业发展、财政扶贫、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 |
Y |
|
12 |
交通运输 |
3487.42 |
公路建设支出。 |
Y |
|
13 |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
515.40 |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补助。 |
N |
|
14 |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
474.91 |
商贸流通服务业和外经贸发展资金。 |
N |
|
15 |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
181.36 |
国土资源气象事业发展资金。 |
N |
|
16 |
住房保障支出 |
1859.68 |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配套基础设施及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
Y |
|
17 |
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
380.99 |
成品油应急储备贴息和基本建设支出。 |
N |
|
18 |
其他支出 |
233.04 |
部分基本建设支出、用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统借统还借款安排的支出、国债转贷资金转拨款。 |
N |
|
合计 |
19265.86 |
|
| |
注:Y-与人口关联程度紧密,N-与人口关联程度不紧密。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3月26日财政部《关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说明》归类。
2.现行转移支付与“户籍人口”挂钩
转移支付项目的资金怎样分配,笔者缺乏相关的资料。但是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确定,财政部有一个书面的文本。本文就以此为例作一些剖析。
现行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考虑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海拔、温度、少数民族等成本差异,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凡标准财政收入大于或等于标准财政支出的地区,不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范围。
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增幅控制调整+奖励资金……………………………………………………………………①
标准财政支出分15个项目计算,即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和其他。
在这些项目中,交通运输支出和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特殊支出两项的标准财政支出已经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⑤],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水利与人口无直接的关联。
剩余的八项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均与人口因素有关。问题是,现行规定基本上按照户籍人口及折算后的外来人口为依据计算支出。
(1)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标准财政支出
这四个项目均与人口直接相关,其计算公式为:
四个项目标准财政支出=∑i(∑j各级次总人口×该级次人均支出标准×支出成本差异系数)………………………………………………………………………………………………②
i=省本级、地市本级、县级;j=0,1,2,…该级次行政单位个数;总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⑥]×折算比例
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如果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外来人口为零。折算比例根据外来人口人均财政支出与户籍人口财政支出之比计算确定。
(2)城乡社区事务标准财政支出
城乡社区事务标准财政支出=∑i(∑j((单位建成区面积城乡社区支出×建成区面积×80%+人均支出标准×人口数×人口规模系数×20%)×0.5+实际支出×0.5 ))……………………………………………………………………………………………③
③式中的人口数,市本级是指户籍人口,县旗市和市辖区是指城区人口。
(3)教育标准财政支出
教育标准财政支出的计算公式是:
教育标准财政支出=∑i(∑j学生数×该级次生均支出标准×支出成本差异系数)………………………………………………………………………………………………④
式中的学生数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包含农业转移人口。
(4)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的标准财政支出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出=城市低保人数×城市人均支出标准 ………………⑤
住房保障标准支出=该地保障住房任务量×保障住房单位支出标准+各类棚户区改造任务量×棚户区改造单位支出标准+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量×农村危房改造单位支出标准…………………………………………………………………………………………………⑥
式中的城市低保人数、棚户区与人口有关,但是是否已经包含了农业转移人口,从公式中看不出来。
3.建议将变量“户籍人口”改为“常住人口”
笔者认为,应该完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标准财政支出。这是因为,常住人口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半年(含)以上的人口,他们要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流入人口做到属地管理、同城待遇。
如果中央政府按照②式确定转移支付,那么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非常有利,因为如果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总人口就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这样,可以获得较多的补助,事实上,那些地区很多有户籍的人已经流出了。反之,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就不太有利,农业转移人口虽然也纳入人口基数,但是乘上折算比例之后,获得的人均补助比户籍人口少。笔者主张,②式中的总人口干脆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而且无论户籍人口还是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支出标准都相同。
③式中的人口数,市本级是指户籍人口,县旗市和市辖区是指城区人口。显然,在确定城乡社区事务均衡性转移支付时,没有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城乡社区事务包括城乡社区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住宅、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等多个方面,与农业转移人口关系非常密切,仅仅局限于户籍人口分配资金,与公共服务同城待遇的要求相背离。因此,式中的“总人口”宜改为“常住人口”。
④式中的学生数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包含农业转移人口,从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数量不少,而且增长非常快[⑦],因而,应当明确是常住人口学生数。
⑤、⑥式中的城市低保人数、棚户区与人口有关,应该明确覆盖范围是常住人口。
表6 修正后的标准财政支出计算公式
|
项目 |
计算公式 |
公式号 |
|
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 |
四个项目标准财政支出=∑i(∑j各级次常住人口×该级次人均支出标准×支出成本差异系数) |
② |
|
城乡社区事务 |
城乡社区事务标准财政支出=∑i(∑j((单位建成区面积城乡社区支出×建成区面积×80%+人均支出标准×常住人口数×人口规模系数×20%)×0.5+实际支出×0.5 )) |
③ |
|
教育 |
教育标准财政支出=∑i(∑j常住人口学生数×该级次生均支出标准×支出成本差异系数) |
④ |
|
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出=城市常住人口低保人数×城市人均支出标准 住房保障标准支出=该地保障住房任务量×保障住房单位支出标准+各类常住人口棚户区改造任务量×棚户区改造单位支出标准+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量×农村危房改造单位支出标准 |
⑤ ⑥ |
五、余论与结论:转移支付分配新格局
1.逐步将税收返还和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并入到均衡性转移支付之中
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目的是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均衡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由接受补助的省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另外,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所选取的变量比较客观,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海拔、温度、少数民族等,这使得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大大减少。所以,总体趋势应该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适当加大,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有所减少。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变化正在形成(如表7所示)。然而,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变化不大,尤其是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每年固定在40%略多。从客观、公正等原则出发,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应该进一步提高。
表7 2011-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单位:亿元,%
|
项目 |
2011 |
2012 |
2013 | |||
|
金额 |
占比 |
金额 |
占比 |
金额 |
占比 | |
|
税收返还 |
5039.88 |
12.6 |
5128.04 |
11.3 |
5046.74 |
10.5 |
|
一般性转移支付 |
18311.34 |
45.9 |
21429.51 |
47.2 |
24362.72 |
50.7 |
|
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
7487.67 |
18.8 [40.9] |
8582.62 |
18.9 [40.1] |
9812.01 |
20.4 [40.3] |
|
专项转移支付 |
16569.99 |
41.5 |
18804.13 |
41.5 |
18610.46 |
38.8 |
|
合计 |
39921.21 |
100.0 |
45361.68 |
100.0 |
48019.92 |
100.0 |
注:[]内的数字是指均衡性转移支付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资料来源:财政部:2011-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表》。
(1)税收返还逐步并入到均衡性转移支付中
现行税收返还包括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税收返还、上划中央“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收返还及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等三个部分。
表8 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决算数
|
序号 |
项目 |
决算数(亿元) |
|
1 |
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 |
3965.73 |
|
2 |
所得税基数返还 |
910.19 |
|
3 |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
1531.10 |
|
4 |
地方上解 |
-1360.28 |
|
|
税收返还合计 |
5046.74 |
注:地方上解主要是从2013年起铁路运输企业营业税由中央收入改为地方收入,以2011年收入为基数上解中央。
资料来源:财政部《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表》。
一些学者主张废除税收返还制度,主要理由是税收返还出于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需要,不具备均等化的功能,有悖于公平原则。应当承认,税收返还额的计算采用计数法,并且是环比递增的,的确有其不合理之处;另外,地方获得的税收返还额与企业所在地有关,这样,招商引资项目越多,获得的税收返还就越多。
站在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地区的立场上,税收返还对它们是有利的,贸然取消会减弱这类地区发展经济的动力。可以考虑将税收返还归并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中,这样,既不会对经济发达地区产生不利影响,又可以克服计算不合理的弊端。
(2)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并入到均衡性转移支付中
专项转移支付,本意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事实上,目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太多,而且多头管理。这是与专项转移支付运行机制分不开的。
2000年8月出台的《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规定,“财政部与中央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分配的专项拨款,申请专项拨款的报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地方主管部门联合报送财政部和中央主管部门。”这一条文就在程序上明确赋予了国家部委办参与分配专项资金的权力,由此造成的一个负面后果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随着“部门”走,缺乏一个按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目的进行分配的程序。
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已经具有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性质,几乎与财政支出功能类别相对应,应当逐步归并。那些真正具有“专项”特点的项目,才保留在专项转移支付中。
2.扩充后的均衡性转移支付配置与常住人口挂钩
将税收返还和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再与常住人口挂钩。现有的转移支付分配格局会发生变化。
第一,人口净流入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可能增加,从而改变补助低溢入的状态。一方面,税收返还与政府服务人口的规模相关,原先经济基础好的省(市、区),不仅不会减少,而且有可能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也会有所增加。这样可以舒缓财政支出广化的压力。
第二,人口净流出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可能减少,但是,由于海拔、温度、地表状况、运输距离等因素,仍然是补助高溢入,只不过溢入的程度下降了。这种变化与人口流出紧密相关,既然公共服务的受众减少了,获得的补助也相应减少。况且,新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人口挂钩,一旦人口回迁,补助又会相应增加。新的决定机制更体现出公平原则。
参考文献:
〔1〕Brown,C.V.and P.M.Jackson,1990,Public Sector Economics[M],Basil Blackwell,Ltd.
〔2〕Buchanan,J.M. 1950,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04):588.
〔3〕陈仲常,董东冬.我国人口流动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对力度的区域差异分析[J],财经研究.2011(3).
〔4〕袁飞,陶然,徐志刚,刘明兴.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J],经济研究.2008
〔5〕刘溶沧,焦国华.地区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J],财贸经济.2002(6).
〔6〕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3(3).
〔7〕赵飞飞.万亿财政大挪移 东部输血西部[N],21世纪经济报道.
[①]户籍人口是指公民依照《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户口的人。常住人口是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半年以上的人口。主要包括:除离开本地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户口在外地,但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者,或离开户口地半年以上而调查时在本地居住的人口;调查时居住在本地,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登记户口即所谓“口袋户口”的人。
[②]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地方社会环境的特点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
[③]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2011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12年全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④] 申兵.“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宁波市为案例 [J].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期。
[⑤]交通运输标准财政支出=(公路里程×每公里交通支出×30%+常住人口×人均交通支出×20%+县个数×县均交通支出×10%+民用汽车拥有量×车均交通支出×10%+面积×单位面积交通支出×30% )×地表起伏度系数。
[⑥] 财政部《2012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采用这个提法,此处不作改动。下同。
[⑦] 事实上,由于东西部地区教育质量的差异,很多孩子并不是跟随父母而是跟随亲友到东部地区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