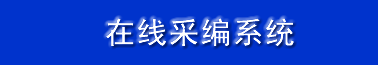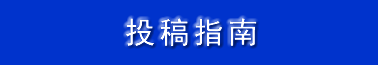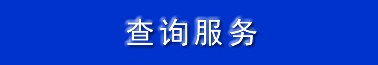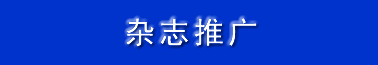张雷宝/内需不再“内虚”的策略选择
浙江财经学院
内容提要: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两种路径机制的比较分析,本文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支柱”的现实支撑力进行了经验性考察,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扩大内需战略有市场主导的消费需求驱动模式和政府引导或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两种类型可供选择,不同的需求驱动模式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和适用条件。(2)扩大内需战略的关健着力点,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主要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非政府消费需求),而基于多重评价标准的分析,目前我国消费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处于严重的“虚位”状态,且虚位率约26%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需求则存在明显的“虚胖”现象并引发了不可持续风险。(3)从根源来看,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国内整体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政府投资扩张冲动的“帮凶”。最后,本文提出了扩大内需政策也须转型升级以及坚持“双轮驱动”策略并渐进改善内需结构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扩大内需 消费驱动 政府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扩大内需政策也应转型升级
在2010年“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战略”基础上,2011年底我国中央政府又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施政主张,即历史上第一次将扩大内需明确为全国经济工作践行“稳中求进”总基调的“战略基点”。理论和实践都易于证明,扩大内需战略已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例如,2008年美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约为92%,印度约88%,中国仅72.8%(王杰,2011)。从此角度讲,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巨大。但须进一步思考的是,自1998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实施以“扩大内需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为什么十多年间我国的内需“扩而不大”问题始终存在?现阶段基于世界金融危机“二次探底”风险的“扩大内需战略”应如何实施才能规避“走老路”风险与政策困境?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与探讨,无疑有助于确保“内需主导型”政策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当然,1998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扩大内需问题已有较为热烈的讨论与争鸣。例如,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大小问题(刘国光,1999)、扩大内需中的分配关系调整问题(杨帆,1999)、扩大内需中的市场信心、消费行为、政策导向及其渐进变迁等问题(杨宜勇,1999;唐财斌,2000;鲜祖德等,2003;戚义明,2009)以及政府投资主导型扩大内需政策缺陷(戴园晨,1999;郭文轩,2003)等方面的探讨都有一定现实意义。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的困惑性思考也同样有启发效果(陈伯庚,1999;王杰,2011)。尽管如此,基于当下困境的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些基本理念还有须澄清之处,扩大内需的路径机制也较为模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及其协同搭配问题也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扩大内需中消费需求的“虚位”现象及其剖析
理论上,经济增长和政府投资的目的就是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最终实现国民幸福最大化目标。然而,已有的研究和大量的数据都表明,目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且呈现不断恶化趋势,明显与我国GDP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消费需求“虚位”现象是目前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现实基础。这里,主要有四大判断标准:(1)以消费率较高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评价基准。例如,按世界银行统计,美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高达84.7%,与之相对应,我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只有56.1%。(2)以典型发展中国家为评价基准。例如,在“金砖四国”中,近十年间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均主要源于内需拉动,平均消费率分别为80%、68%以及51%,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是最低的45%左右。(3)以世界平均水平为评价基准。例如,近二十多年来与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8%,而2009年我国消费率只为45.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4个百分点。(4)以改革开放以来至分税制之前的历史平均水平为评价基准。1980-1994年间我国平均消费率约62.45%,而1995-2010年间的平均消费率约44.05%。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不仅一直低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率,且近年来与自身相比基本处于不降趋势甚至屡创历史新低。如表1所示,无论从哪个评价标准来看,我国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处于严重“虚位”状态,且平均虚位率约26%。基于这种巨大“落差”,国内甚至有专家提出要制定提高消费率的“硬性指标”并采取“硬性措施”(罗云毅,2012)。
表1:基于不同评价标准的我国消费率“虚位”值估测及其比较
|
评价标准及其数值选定 |
中国情形 |
消费需求“虚位”率估算 |
|
美国 (1990-2010年间的平均消费率,即84.7%) |
中国 (1990-2010年间的平均消费率,即56.1%) |
33.76% |
|
“金砖四国” (1996-2006年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四国平均消费率的平均值,即61.5%) |
中国 (1996-2006年间的平均消费率,即44.6%) |
27.48% |
|
世界平均水平 (1990-2009年间的平均消费率,77.8%) |
中国 (1990-2009年间的平均消费率,44.4%) |
42.93% |
|
1980-1994年间的中国 (平均消费率,62.45%) |
1995-2010年间的中国 (平均消费率,44.05%) |
29.46% |
注:消费需求“虚位”率指标是指中国消费需求落差值占评价标准的比重。
资料来源:罗云毅:“扩大消费与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之辨”,《中国投资》,2012年第1期;吴婷:“‘金砖四国’消费率水平中国最低”,《上海证券报》,
应该说,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即主要指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非政府消费需求)。对居民消费需求来说,能否自然扩大及其扩大程度无疑主要取决于三大经济变量或需求条件:(1)国内居民“有钱花”,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长及其结构均衡条件。可以说,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常修泽,2009)。此外,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程度也将对扩大内需战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例如,根据2011年我国民政部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总人数高达7516.4万人(年度降低率仅0.64%),而从结构来看,我国城乡低保人数呈现“
三、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虚胖”现象及其剖析
自1998年实施以“扩内需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路径特征,政府投资的“发高烧”与消费市场的“低温度”之间的反差也引人深思,由此引致投资需求(特别是政府投资)的“虚胖”现象。投资需求的“虚胖”现象的判断和认定,主要是基于如下分析:(1)内需结构中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即大多数国内文献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例如,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2009年甚至高达66%;(2)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例如,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多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甚至高达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我国2009年的最终消费率为48%,却比2000年下降14.3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马建堂,2011)。(3)与高投资率、高资本形成率相伴随的是低投资效率。例如,我国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从1992年的47%左右降至2009年的14%左右(如表2所示);(4)具有“透支未来”特征的政府大规模投资。研究表明:在地方财政预算内资金基本属于养人、养机构的“吃饭财政”条件下,目前我国各地方的政府投资非效率问题,一方面体现在政绩性投资需求中的“泡沫”过大、水分过多,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土地财政”和“债务财政”双重政府投融资模式所蕴藏的巨大财政风险。例如,若加上地方政府直接债务,2009年末我国各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规模估计约11万亿,即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①]。
低效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虚胖”现象及其继发的不可持续风险,势必引发如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源泉何在?显然,这种高投资率与低产出率引致的巨大风险昭示了扩大内需保增长过程中“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的必要。
表2 1992年-2009年我国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变动趋势分析
单位:亿元、%
|
年份 |
GDP (当年价格) |
GDP指数 (上年=100) |
增长率 |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 |
名义投资率 (IGDP) |
边际产出资本 比率(IOCR) |
|
1992 |
26923.5 |
114.2 |
14.2 |
8080.1 |
0.30 |
47.32 |
|
1994 |
48197.9 |
113.1 |
13.1 |
17042.1 |
0.35 |
37.05 |
|
1996 |
71176.6 |
110.0 |
10.0 |
22913.5 |
0.32 |
31.06 |
|
1998 |
84402.3 |
107.8 |
7.8 |
28406.2 |
0.34 |
23.18 |
|
2000 |
99214.6 |
108.4 |
8.4 |
32917.7 |
0.33 |
25.32 |
|
2001 |
109655.2 |
108.3 |
8.3 |
37213.5 |
0.34 |
24.46 |
|
2002 |
120332.7 |
109.1 |
9.1 |
43499.9 |
0.36 |
25.17 |
|
2003 |
135822.8 |
110.0 |
10.0 |
55566.6 |
0.41 |
24.44 |
|
2004 |
159878.3 |
110.1 |
10.1 |
70477.4 |
0.44 |
22.91 |
|
2005 |
183217.4 |
110.4 |
10.4 |
88773.6 |
0.48 |
21.46 |
|
2006 |
211923.5 |
111.6 |
11.6 |
109998.2 |
0.52 |
22.35 |
|
2007 |
257305.6 |
113.0 |
13.0 |
137323.9 |
0.53 |
24.36 |
|
2008 |
300670.0 |
109.0 |
9.0 |
172828.4 |
0.57 |
15.66 |
|
2009 |
340506.9 |
109.1 |
9.2 |
224598.8 |
0.66 |
13.95 |
注:IGDP(名义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100%;IOCR(投资效率)= 增长率/IGDP。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
应指出,我国扩大内需过程中的投资需求“虚胖”现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根源来看,政府投资冲动显然是导致国内整体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在政绩锦标赛作用机制下,“铁打的地方流水的官”,政府官员投资决策短期化特征明显,即追求政绩最大化目标的公共财权资本化风险问题客观存在。由于特定政绩考核制度下政府投资冲动的形成机制往往难以根除,因此产生的强烈政府投资冲动也势必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扩张(如政府主导的以“招商引资论英雄”活动)。必须看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身为破解地方政府“投资之謎”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脚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解读地方政府“小财政、大投资”之惑的重要钥匙[②]。
四、基本结论与若干建议
自1993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风调雨顺”的时候少,而“风雨飘摇”的时候多,国内外各种危机因素始终存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府对“扩大内需保增长”型宏观调控政策的依赖。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惯性思维和干预传统,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带有较强烈的政府投资主导色彩就不难理解。
本文的分析研究至少表明:(1)扩大内需战略客观上有市场主导的消费需求驱动模式和政府引导或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两种类型可供选择,不同的需求驱动模式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和适用条件,而我国政府基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选择了后者。(2)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着力点,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主要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非国内投资需求。基于多重评价标准的分析,目前我国消费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都处于严重的“虚位”状态,且虚位率约26%;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需求则存在明显的“虚胖”现象并引发了不可持续风险。(3)对居民消费需求来说,能否自然扩大以及扩大程度无疑取决于三大经济变量或需求条件:国内居民“有钱花”,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长及其结构均衡条件;国内居民“敢花钱”,即未来收入预期以及社会民生保障条件;国内居民“有地方花钱”,即消费热点以及市场制度环境条件。(4)从根源来看,政府投资冲动显然是导致国内整体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政府投资扩张冲动的“帮凶”。
可以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意料之中”地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战略基点”,而改变消费率低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中的顽疾也正成为值得期待的改革“突破口”。为此建议:(1)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从传统的政府引导或主导下的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需求驱动模式转型,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驱动模式的完全转换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坚持投资与需求“双轮驱动”策略并渐进改善内需结构的政策更符合国情。(2)国民收入总量分配政策上,从注重旧的“两个比重”(即1994年我国政府提出的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向提升新的“两个比重”(即2009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切实转变[③]。(3)基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的理论假设,结合公共行政以及民生财政等基本理念,有效构筑“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的“双底”战略应是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本文认为,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防范“资本剥削劳动”风险的重要制度保障,而加大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则是公共财政的政策“底线”所在,两者对扩大内需战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4)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四道“闸口”(即发改部门、财政部门、政府采购部门、绩效管理与审计部门等)协同运作机制,控制政府投资体量“虚胖”,优化政府投资内部结构,提升政府投资绩效水平。在此“闸口”监管机制中,突出和强化政府投资绩效目标考核制度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例如,可考虑明确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的三种制度规则:先定绩效目标再给钱(如控制初始投资);先做绩效评价再拨款(如控制追加投资);先搞绩效排序再安排(如控制盲目投资)。(5)外部制衡层面,加大体制外监督制约,不断改进消费率驱动的“虚位”状况,有效抑制政府投资的“虚胖”趋势。例如,2005年以来浙江温岭实行的“参与式预算”民主理财模式,对保障和改善区域民生消费,控制政府投资非理性膨胀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然,这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宝贵且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陈伯庚.论消费政策调整.经济学家,1999年第1期.
〔2〕刘国光等.扩大内需还有文章可做”.中国改革,
〔3〕杨宜勇.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经济参考,
〔4〕杨帆.启动内需 重在调整分配关系.中国财经,
〔5〕戴园晨.投资乘数失灵带来的困惑与思考.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6〕唐财斌.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选择.税务研究,2000年第1期.
〔7〕鲜祖德等.从农民消费行为看扩大内需的对策”.统计研究,2003年第8期.
〔8〕郭文轩.积极财政政策执行效果与隐忧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9〕戚义明.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发展.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
〔10〕王杰.扩大内需,路在哪里.浙江日报,
〔11〕马建堂.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需要改善.人民日报,
〔12〕罗云毅.扩大消费与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之辨.中国投资,2012年第1期.